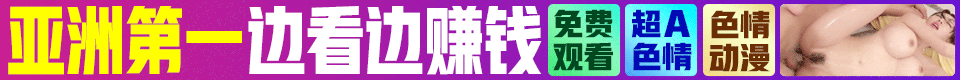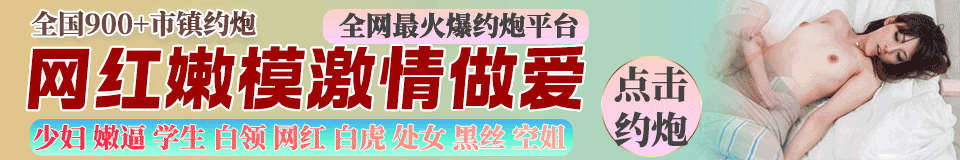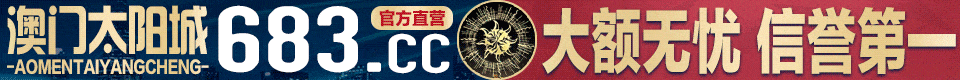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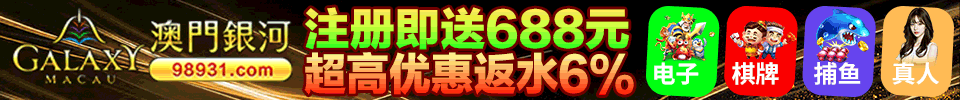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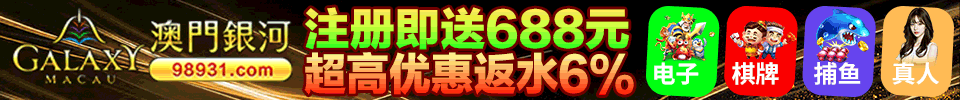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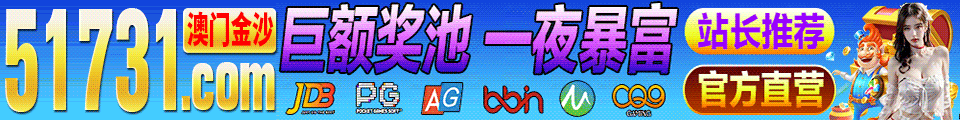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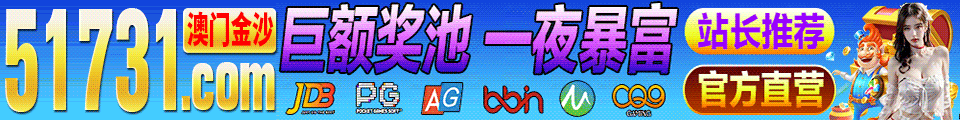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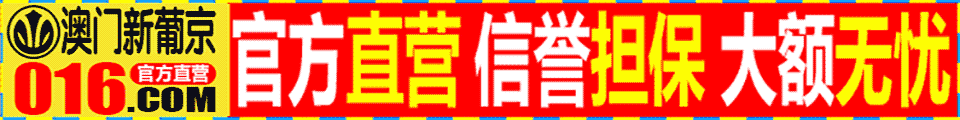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








处女膜破坏小组
在大四的那一年秋天,我终于与相恋了三年的女友分手。我觉得我还很爱她,可是她却和一个研究生準备一起出国,去海的另一边寻找幸福。
那是个金色美丽的秋天,在漫天黄叶中我只有一个人暗自神伤。
后来,就在那个秋天,我认识了小军,小强和小刚。和他们一起组成了这个“处女膜破坏小组”。
他们三个都已经离开了学校。小强和小刚已经上了几年班,早就冲到了劳动生第一线。小军中专毕业,不知不觉在黑道上混了许多年。
认识他们时,我还在纯洁的失恋痛苦中挣扎着,在一间昏暗的小酒吧,用我身上的最后几元钱买醉。
他们三个与我一样,也刚刚被女友甩掉或者刚刚甩掉女友,心情都不好。
于是我们在肚子里装满酒精之后,糊里糊涂地认识了。
组成这个“处女膜破坏小组”最初是我们的一个玩笑。我们出于失恋的苦大愁深,发誓要强暴一个个处女,用她们最珍贵的血液,祭奠我们都已逝去的纯洁感情。
我们的口号是:对待天下的处女,要玩弄她们的肉体,摧毁她们的精神,践踏她们的人格,摺磨她们的灵魂。
这个玩笑最后变成了现实。小刚他们很认真地组织着我们每个周末的活动。每个人都很执着,以破坏处女膜作己任,坚定的破坏着一个又一个的处女膜。
那时候,我还是个处男。我对性的体验仅仅停留在和女友的热吻上。
但是,认识他们三个之后,我在性方面的进步简直称的上一日千里。
小强小军都算是泡妞高手。比起他俩来,小刚更是高手高手高高手。
他总能在最短的时间最关键的场合泡到最值得他去泡的妞。对小刚来说,乱军之中取美女内裤,犹如探囊取物。
我也还算英俊,虽然赶不上刘德华,起码扯平了周润发。所以总有女孩子愿意主动靠近我。
再加上我不断地虚心向小刚他们学习,于是很快也就忘掉了我那满脸雀斑的大学女友。
每个周末的月黑风高之夜,就是我们处女膜破坏小组的行动之时。
其实我们并不强暴,也不轮姦。我们只是很认真的互相寻找和介绍女孩认识,然后想方设法去验证她们是处女,最后和她们上床。
我们每次用处女们的贞操之血,把卫生纸浸红。再用它们做成一朵朵小纸花。这种小纸花我们在上幼稚园时就会做。只不过儿时的小纸花纯洁的像孩子天真的笑脸,现在的小纸花却昭示着处女们贞操的堕落。
我所做的第一朵小纸花,是一位漂亮的小学女老师用贞操之血染红的。她实在是一个很漂亮的姑娘,刚刚从师专毕业分配到一所小学教语文。
小刚把她介绍给我,并低声耳语对我说:“这女孩纯着哪。我还没动,保证是处女。”跟她认识了没两天,我们就在她的宿捨上了床。
那是我的第一次,也是她的第一次。当我进入她的身体时,她紧皱着眉头髮出一阵呻吟。我觉得淫蕩极了,真难以想象她是如何站在课堂上道貌岸然地给学生们讲课的。
完事后,我坦然的用早準备好的卫生纸蘸她的血。她竟然没问什,只是羞红了脸看我。
做成第一朵小纸花后不久,我就把她甩了。这个女老师虽然漂亮但我并不爱她。
我只是做我的小纸花,我不想跟她终身私守。
她是第一个,但不是最后一个。从她之后我凭藉不断积累的经验,追逐着一个又一个的处女,破坏着一个又一个的处女膜。
和小军小刚小强他们在一起,我的确学得很坏。我们从不自己的行负责,也从不什事而后悔。我们只是虔诚地用女孩子们的鲜血做小纸花,彷彿做这种纸花是一个比性爱比理想还要高贵光荣的事情。
这个世界很可笑。当我还是处男时,我所听到的全是世界上处女越来越少这类令人紧张的话语。可是在我成“处女膜破坏小组”成员之后,我发现这个世界上的处女真的还很多,多到我们小组忙得精尽人亡全军覆没。
可笑的是,每个处女都喜欢跟你谈论性,谈论性伦理。她们虽然没有性经验,却在这些方面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而且似乎每个处女都处在性饑渴之中,随时愿意跟男人上床,从而告别传统的贞操纯洁时代。
我觉得很奇怪。过去书本里描写贞洁的神圣在现实中竟然已变得分文不值了。这算是对人伦的背叛还是道德的发展?
我问过小刚:“什是纯洁?”他的回答是:“多做爱,少做梦。”
道理很明白,还能多说什呢?
小刚已经做了十四朵小纸花。他每次我们展示这些战果时,脸上的笑容是纯洁的。
小强也做了十朵小纸花。他的工作比较忙,所以时间精力有限。小军做的最少,至今才做了三朵。
除了我给他介绍的几个大学女生,其余的女孩上床之后总令他失望不已。他总遇不到处女?
小刚分析指出,小军整天跟那帮坐台小姐混在一起,认识的女孩没几个好货色,他早就失去了分辨是否是处女的能力了。
一个冬天下来,我竟然也做了五朵小纸花。每一朵上都红豔豔地蘸足了鲜血。事实上我共和七个女孩上了床,可其中两个不是处女。认识她俩是我瞎了狗眼。我花了最久的时间和最大的努力与她们发展关係,可是最后得到满足的却是她们。
冬去春来。
我日复一日的应付着学业和虔诚製作着这种贞洁纸花。
我觉得自己都开始带有后现代主义的崇高气质了。
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什都无所谓,甚至包括女孩真情的眼泪。
回忆起我刚被女友甩掉时的悲伤,我只能龇着嘴从牙缝里蹦出“傻冒”二字。我想我不会再像以前那傻,我过去的单纯无知早就和那些处女膜一起被我毁灭了。
剩下的我,只有极富性能力的躯壳和专业的泡妞精神。灵魂纯粹死亡了。我以为我会就这样半死不活的过下去,直到衰老,直到死亡。
但是,生活总有改变。世界每天都有奇。
在大四最后的春天,我奇般地爱上了被我破坏的第六个处女。
这个女孩正在上高三。她长得不算太漂亮,但是很清纯,每天都秀秀气气的,笑容天真拘谨,你一看就知道是个学生,而且还是个处女。
认识她是在市图书馆。由于要準备大学的毕业论文,我就坐在阅览室她的对面用功。当我们同时起头时,我冲她笑了笑,我们就认识了。
她叫萧婷。我更愿意叫她小婷。
看的出来,她在学校是个学习不错而且非常有理想的女孩。我认识她时,她的书包里还装着一本《牛虻》。
她抚摩着《牛虻》的书皮,很认真地告诉我:“这本书描写的是灵魂的坚强和不屈的理想。”
小婷还很单纯,充满着对未来的想望。
而我,除了做小纸花,几乎没有什坚强的灵魂和不屈的理想。
所以我不是牛虻,我是流氓。第二天晚上,我就和小婷上了床。
我也曾经高考过,理想过。因而我清楚地明白像小婷这样纯纯的高三女生想听什,爱听什。那个晚上,我约她到我在校外租的一间小屋里。月亮很圆,窗外一只发情的猫在嗷嗷乱叫。
我给她讲高考的心得体会,讲坚持和忍耐,讲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,讲存在主义哲学。当我觉得她看我的眼神中带有一丝仰慕崇拜时,我準确的把握了机会。
我不是一个新手。我从到用手指触摸,让她难以自製。最后我进入她的身体时,她紧紧抱住我,发出一声惨叫。那凄厉的叫声在宁静的夜空中久久回蕩。
那个夜晚我非常兴奋。小婷的鲜血染红了很大一张卫生纸。我决心要用它做一朵大大的花朵。
小婷依在我怀中,轻轻抚摩着我的臂膀。她的眼神仿佛依旧纯洁,就像九寨沟的海子,宁静安详。
但是我知道,她已经不再是处女,她被我糟蹋了。
于是,我搂着她兴緻勃勃给她讲我们的处女膜破坏小组,给她讲我们做的小纸花,给她讲我们的口号,讲我那几朵纸花。
小婷一句话也不说的听着,她的脸色很苍白。因她突然明白,她被玩弄了。
我永远记得那一刻。小婷愤怒地起身穿衣服。她的动作非常好看,翩翩冉冉,像在舞蹈。
好像下身还很疼痛,她穿好衣服后用手捂着小腹,弯腰站了一会儿。
我看到她的肩膀在抖动。她一定是在哭。
临出门前,小婷咬牙切齿对我说:“你把我毁了,你是禽兽!”她的表情在灯光下像一只野兽,眼睛中放射着仇恨的怒火,可脸上却满是泪水。
她是喜欢我的。她一哭我就明白了。
于是,我笑出声来。在笑声中她走了,头也不回的走进茫茫夜色之中。
那天晚上用小婷染红的纸,我认真地扎成了一朵最精緻的纸花。这朵纸花是我所做过的最好的,美丽均匀,近乎完美。
扎完后,我的眼泪就从脸上滚落下来。不是懊悔也不是悲哀。只是想哭,莫名其妙地想哭。哭泣是不需要理由的。
小婷一哭,证明她是喜欢我的。我一哭,我想我也喜欢上了小婷。
过了几天我去找小婷。这是第一次我回头去找我所破坏掉的处女。
在她的中学门口,我看到神色黯然的她,一个人背着书包,低头从学校走出来。两条修长美丽的腿,在运动裤的包装下,感到格外诱人。
她一看到我就哭了。我对她说:“我把你毁了,所以我要你负责一生一世。”
小婷一定非常感动。她的眼泪弄湿了我的衣襟。
晚上她没有回家,和我一起回到了我的小屋。我们在床上像蛇一样缠在一起。
小婷说:“你对我真好。”她的话让我很奇怪。我跟她做爱只是了满足我爆发的慾望。我并不想对她多好。甚至下午说要负责她一生一世的话,我也没当真。她又什会觉得我对她好呢?
我喜欢小婷也许是因她有人格,而我没有;又也许我喜欢小婷是因她有理想而我的理想早没了。这种喜欢就像因你没钱从而喜欢上一个有钱人一样,我以是卑鄙的。
但小婷不这想。她愿意用她不多的零花钱给我买好吃的甜米饼,愿意每天放学后尽可能多的呆在我这里。她说她喜欢看着我,
说我有时坏坏的很像杨过。她希望自己是小龙女,这样我们之间就会有天长地久的爱情。
我还不想从处女膜破坏小组退出。但有小婷跟着总是不太方便。好在那段时间我在忙毕业的事,所以没有什尴尬的情况。
写大学的毕业论文就像拉屎一样容易,我一蹲就是一大堆。拉完毕业论文,在六月份,我就光荣的毕了业。
有个亲戚在热忱地帮我联繫工作,而我自己却无事可做。
这时小刚来找我,告诉我他找到三个前卫少女,保证个个是处女。
他约了小军,我们三个将在我租的小屋里上演三驾齐驱的好戏。驱的自然不是马车,而是老汉推车。这三个女孩果然前卫而叛逆。
她们很愿意在这个双月双号星期双来告别自己的处女生涯。
于是我那张不大的床上,三驾推车在性的原野上驰骋奔腾。
果真全是处女。三处鲜红的血让我觉得亢奋不已。我身下的女孩除了乳房丰满之外,号叫也格外诱人。
身旁小军的粗野让她身下的那个女孩有些吃不消。小刚边忙自己的边教训小军:“慢点,注意节奏。”说得就像是在跳交谊舞。
就在我们六人高潮起时,房门被推开,小婷走了进来。她手里还提着我最爱吃的甜米饼。
看到我们六个人赤身裸体,保持着令人兴奋的姿势,她被眼前的一切惊的目瞪口呆。如果说她以前骨子里还很纯洁的话,那看到这一切,她的灵魂就算是被玷污了。
所有人都看着我,等待着我在这种尴尬的气氛中找到一个解决办法。
我只好责怪小军:“你最后进来也不知道把门反锁上。”
小军挠着头皮嘿嘿直笑。在不是黑社会打架的日子里,他的笑容还挺可爱。
小婷握着拳头质问我:“你说过你会我负责一生一世的,你••••••”
她自己也不知该说什好。
那时我的手还放在一个乳房上。我摸着这个乳房,用学生式的口吻告诉小婷:“你无权干涉我的私生活。我不爱你了,你赶快滚蛋吧。”
听到这话,小婷的眼泪哗哗地流了下来。
我又礼貌地说:“出去时记得把门锁上。”说完,就接着做我的爱。
小婷是怎哭着飞奔出去的我已不记得了。
最后和这三个女孩道别时她们也没提这件事。
她们的贞操刚刚失去,我想她们一定都有点后悔。
临走时小军对我说:“你太没人性了。”他的口气中充满着敬佩之情。
能让一个黑社会佩服,我感到非常得意。
我也知道小婷是不会再来找我的,我们之间完蛋了。好在我又用今天一个女孩的贞操之血,做了一朵小纸花。已经七朵了。七个仙女在我的破坏下,最重要的一层薄膜都随风而去。怎说也算是一种成就感。
在成就感的满足中,我还是觉得空虚。
这种空虚像夜晚茫茫的夜空吞噬着我的心灵。我今天伤害了小婷,用玷污她肉体的方式再次毁灭了她的心灵。离她高考仅有一个月时间。
我希望她能考个好大学,这样她也许就不会怨恨我一辈子。
我的愿望是善良的。这一刻我以为自己算是个好人,我欺骗着自己,从而得到了心理的安宁。
可是后来,我从小婷的同学那里听说,小婷的高考失败了。
那天大约是小婷高考后的一个月左右,我难以抑製地想知道小婷考到了哪座城市,于是不自觉地走到了她们学校高考的榜单前。
那是夕阳夕照的傍晚,小婷的中学里飘散着桂花的香气。这种气息我曾经在小婷身上闻到过,所以感到特别亲切。
榜单前一个女生对我说,小婷的高考失败了。这是个大辫子的女孩,长着漂亮的黑眼睛。她又意味悠长的告诉我,小婷在高考前就崩溃了。她的精神在高考前似乎受到了什猛烈的打击。在前几门没有考好之后,最后的两门考试她都没有参加。她放弃了。
这个大辫子的女孩又告诉我,小婷本来是他们班的前三名,老师们都对她寄予厚望,觉得她本应该考上名牌重点大学。
我听着这些话,突然想起小婷曾经对我说:你把我毁了,你是禽兽。
我不觉得我做错了什,我只是觉得自己很可耻。
出于自卑的心理压力,我努力地讨好着这个大辫子女孩。我不断地逗得她爽朗发笑,最后和我一起,在我租的那间小屋里上床做爱。
这个大辫子女孩不是处女,她说她和她男朋友曾经在高二时试着做过。
我根本不在乎她是不是处女。最重要的是她是小婷的同学。所以我用力的干她,让她发出痛快的号叫。我在这种叫声中寻找着灵魂的精华和罪恶。
我一直和这个大辫子女孩保持着联繫。因通过她,我能够知道小婷在哪里,小婷在做什。
大辫子考取的是我刚毕业的那所大学。一开学她就把辫子剪成不到一指长的短髮,人也就变得说不出的丑陋。
她晃着一头短髮,歪鼻子斜眼的告诉我,小婷在一所很一般的补习学校补习。
我没有勇气去找小婷,因我觉得看见她后我可能会内疚。我还是喜欢她的。每当我和一些其他的女孩子上床时,我就会想起她,想起她第一次做爱时发出的惨叫。
这段日子我找到了一个机关工作。上班时间除了扫地提水巴结科长之外,就是大量阅读报纸书籍。
自然周末也少不了参加处女膜破坏小组的活动。这种有意义活动的参与结果就是:到我再见到小婷时,我已经做齐了整整二十朵小纸花。
小婷的话还是最鲜豔最精製的。看到这朵花,我就总是想念她。
最后,在小婷準备第二次参加高考的两个月前,我决定要见见她。
我的本意是鼓励鼓励她,所以我去了她的补习学校。
她比一年前明显胖了一点,脸色苍白了更多。每个补习的女生都会这样,我一点也不觉得奇怪。倒是我的出现出乎了小婷的意料。看到我时,小婷的眼泪像断线的珠子一样落在地闆上。
我们彼此注视了很久。我说:“祝你今年高考顺利。”
她慢慢走过来,狠狠抽了我一个嘴巴,然后伏在我怀里放声大哭。
那天晚上,我们回到了我的宿捨。我已经跟单位要了间单身宿捨,不再租那间可怜的校外小屋了。
在床上,我用行动告诉着她这一年我有多想念她。她也无声地配合着我。那张宿捨的小床在黑暗中发出叽叽嘎嘎的欢叫。
彷彿我和小婷做爱,这张床最快乐。
我觉得我和小婷和好了。于是很虔诚地给她看我所做的二十朵小纸花。我对她说:“你就是其中那朵最大最精緻的。”
她的脸色刷地变了,变得没有一点血色。她生气了。她知道我还在不断地破坏着处女膜。她是第六个,一年时间却多了十四个。我不但没有学好,反而变得更坏了。
那天晚上,她连夜就走了。我不知道她身上有没有装着足够打车的钱,但我知道小婷一定恨我恨透了。
有人说过,高考就像做爱,第一次是最重要的。男生女生都一样。
在第一次之后,男生就越来越油条,女生则越来越烂。
小婷的第一次高考失败了。第二次也同样失败了。
只不过第二次我没有怎刺激她,是她自己失败的。
当然我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因在高考前几天,小婷发现自己怀孕了。
高考落榜后,小婷来找我。那时我正在宿捨和小刚对诗。身边坐着一个明眸浩齿的女孩。这个女孩说我和小刚谁的文采好,她就把她的贞操献给谁。
小刚吟了一首《春晓》:春眠不觉晓,处处性骚扰。夜半呻吟声,姑娘变大嫂。
我受过高等教育,当然不肯轻易认输。所以我出了个上联,只要小刚对出下联,我就乾拜下风。我的上联是:月经带,月月带,越带越经带。
这是个千古绝对。小刚一肚子大粪,根本没法对上来。眼看他就要认输离开,把这个女孩让给我时,小婷来了。
小婷的眼睛有点肿,她说:“我怀孕了。”
我无话可说。我很健康她也没有生理问题。这是很自然的事情。
我的冷漠让小婷很愤怒。她扬着拳头说:“你毁了我。你是个禽兽!”
这句话我以前就听过,很耳熟很亲切。
她又说:“我恨你一辈子。”说这句话时她似乎又变得平静了。
说完,她扬长而去。
她变得有点尖刻有点坚强。我想这也许是因读了《牛虻》的缘故。
我也曾读过《钢铁是这样炼成的》,但我依旧没有什高尚的品质。
像小婷这样,能充分从书籍中吸取力量的女孩,我是佩服的。
小婷这一走,我就两年没有再见过她。
这两年的时间里,我们处女膜破坏小组的活动也渐渐减少。我们四个都觉得有点乏味了。原来,生活中所有的东西都会慢慢让人厌倦,没有什是永远值得去做的。我们活着还有什意思呢?
两年的时间,小军已经从黑社会打手的身份混到了一个小头目的地位。小强发了财却阳痿了。他对钱财的渴求远远超越了对性的慾望,很变态。
只有我和小刚还同过去一样。在平乏与无聊中,浪费着光阴。
这段时间里,我读了一本很令我感动的书。
书名叫《也许痛苦,未必幸福》。
作者乃纲在他的序言中表示他写的是感情,而我却从那本书中读到了过去的纯洁。
这种高尚的感情我几乎已经忘记很久了,没想到一本书又让我看到了曾经的人格。我憎恨回忆过去,因这会让人更觉得可耻。
于是感动之后,我立即把这本《也许痛苦,未必幸福》烧掉了。
我要把自己过去的人格,过去的崇高,像邱少云一般化灰烬。
但是,人生中许多事你总是不能不回忆,有许多人你也总是无法忘记。
小婷就是我无法忘记的。两年之中,我眼前总是闪过她的身影,她的表情。我忘不掉第一次见她时,她抚摩着《牛虻》的书皮,很认真地告诉我:“这本书描写的是灵魂的坚强和不屈的理想。”
我觉得这句话是她的一面旗帜,展示着她纯洁外表下的高贵品质。
我想念她。我发现思念让我更加爱她。如果我再见到她,我想我一定还会对她说:“我把你毁了,所以我要负责你一生一世。”有一天下着大雨,小军告诉我他见到了小婷。
小军的老大开着几家有色情服务的歌舞厅夜总会。
小军看见小婷在那里面当坐台小姐。
顶着大雨,我立刻连夜奔进了那家歌舞厅。看到小婷时我几乎不肯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她穿着件女孩最隐秘部位都一望无余的白短裙,侧身坐在一个老得可以做她父亲的男人腿上。
那个男人肥胖丑陋的大手,正在小婷已经不能再短的短裙下肆意乱摸。
小婷撒娇地说:“赵老闆,你坏死了。”说完,她看见了我。
那一刻我以小婷会哭泣。可是她没有。她向我笑了笑就继续让那个老男人乱摸。我哭了。我知道我真的把小婷毁了。
我冲过去,拿出身上全部的钱摔在那个老色鬼的脸上,告诉他这个小姐今晚我包了,然后拉着小婷冲了出去。
我把小婷拉到大雨中,我质问她:“你还记得《牛虻》吗?”
她哼了一声,说早忘了。雨水打湿了我们的衣服,也沖掉了小婷脸上厚厚的化妆品,他终于又变得纯洁而楚楚动人了。
我带她回到了我的住所。单位已经给我分了一套房子。窗外雨不停地下,像几千年人类悲哀哭不尽的眼泪。
小婷点燃香烟,给我讲了她这两年的生活。在第二次高考落榜后,她心灰意冷。
再加上怀上了我的孩子,一个不到二十岁的女孩,她所承受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。
她打了胎,然后在几个地方上过班,最后在酒吧做起了小姐,自然而然地经过了从不卖身到卖身的过程。我对她说:“记得我的话吗?
我说过,我把你毁了,所以我要负责你一生一世。”
她冷笑一声,说:“我已经不是过去的小婷了。现在的我不再单纯幼稚了。我再也不会去相信这种你们臭男人说出的鬼话啦。”
她起身要走,临出门前又转过头留给我她的手机号码,告诉我如果想嫖妓就给她打电话,她收我半价。
我想追她回来,可是我做不到。她的确已经不再是小婷了。
透过窗户,我看到她在楼下的雨中站了一会,任由雨水无情地沖刷着她的身体。
我想她一定在哭。
我觉得如果我冲下楼在雨中拥吻她,那我们一定会重归于好。
但是我错了。
就在我想但还没有冲出门时,我看到小婷转过脸恶狠狠向我这栋楼吐了口痰。那一刻正好一个闪电,雷电的光辉照亮了整个夜空,也叫我看到了小婷充满恶毒怨恨的眼睛。她是非常恨我的,我肯定。她的眼睛像恶魔像泼妇像毒蛇。过去那种九寨沟海子式的宁静清澈已经彻底地消失了,没有了。
我觉得很害怕。一声闷雷之后,我坐倒在地上。我把小婷毁了。
我托小军照着点小婷,小军在那些夜总会舞厅很吃得开。小军说:
“一个婊子也值得你这上心。”
我听了这话真想揍他,但估计打不过也就算了。
从那以后,我也见过几次小婷。我约她出来,她都拒绝了。她说如果我要嫖她就到她们的夜总会去。
为了见她,我也只有去嫖她。有时我一个人去,有时我和小刚一起去。
记得那一次我和小刚一起嫖完她后,她拍着我的肩膀,说我的身体还和原来一样棒。说话时她身上散发着浓郁的劣质香水味道,早已没有了学生时代淡淡的桂花香气。
再后来,小婷死了。她染上性病,治了几次没有治好,烂死了。
我知道,她的性病不是药物就能治好的,因她的腐烂是从灵魂深处开始的。她曾经是个很有理想很纯洁的女孩,身上曾经散发着淡淡的桂花香气,她也曾经了《牛虻》而振奋。
但是她被我毁了。一个人纯洁高尚的品质一旦被毁掉,那离死也就不远了。
所以,我想也许这个世界上只有我才知道,小婷是怎死的。
小婷遗体告别那天,没有追悼会,没有亲戚,没有朋友。大约他们觉得一个妓女的死是无足轻重的。
那一天天很阴。我们处女膜破坏小组和小婷的母亲五个人告别了小婷。小婷的父亲被她伤透了心,怎也不肯来。
我没有想到小婷的最后遗容是那纯洁,使我看到后立刻就想起了第一次见到她的情景。而此刻的她已不再抹浓暗的口红,不再穿那种卖淫生的职业装。她的脸清纯苍白,嘴角甚至微微带有一丝笑意。她彷彿要很认真地告诉我:
“这本书描写的是灵魂的坚强和不屈的理想。”
我明白,小婷死了。这种纯洁的面容只是安在了一堆死肉上面。
所以,那一刻我后悔了。
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如此的后悔如此的惭愧,我跪在小婷的尸体前,久久地不愿起身。我虽然没有流泪但我的灵魂在流泪。
小婷的母亲在我面前哭得死去活来。如果她知道是我把小婷毁掉的,她会发狂杀了我吗?她不会。因她无法理解我对小婷的毁灭程度。
我想起了我们处女膜破坏小组的口号:玩弄她们的肉体,摧毁她们的精神,践踏她们的人格,摺磨她们的灵魂。
这四样我在小婷身上全实现了。可是我却后悔了。
处女膜破坏小组今天所得到的成就,就是毁灭了小婷。
我想,它毁灭的不仅仅是小婷。我们一共做了一百朵小纸花,就是一百个女孩被我们毁灭了。我们玩弄,摧毁,践踏,摺磨。一百个女孩一百个纯洁成了我们无耻的功绩。
我确实后悔了。
如果小婷活过来,我觉得我已没有资格对她说:“我把你毁了,所以我要负责你一生一世。”
一百朵小纸花摆放在小婷遗体的周围。我把小刚小军小强的纸花全部都要来了。
我要用这一百朵纸花,做小婷的陪葬。我要用这一百朵纸花的贞操和纯洁,表达我对小婷最深的歉意!!!
小婷的遗体和那一百朵纸花一起被火化了。我对小刚他们说:“我们处女膜破坏小组解散吧。”
没人反对。这个组织的确太无聊,无聊到所有人都厌倦了。
于是,这个存在了许久的处女膜破坏小组,终于在一个女孩的毁灭中,彻底的解散了。
从小婷化灰烬的那一天起,我的魂灵就处在深深地后悔当中,这种后悔让我觉得胃在收缩,噁心想吐。
这个城市中到处飘蕩着那许多处女贞操逝去的鬼魂,像苍蝇蚊子一样,无处不在,打扰着我的灵魂。
我决心要离开这个城市。我要改变我自己,我要用一种小婷曾经拥有过的纯洁重新生活。
我买了去最远城市的火车票。我要彻底地告别过去,忘掉小婷,忘掉那些纸花,忘掉处女膜破坏小组。远远地走开。任何人都不会再记得我,我也不要再记得任何人。
坐上火车后,我的心情是兴奋的,我觉得我将要从对小婷的愧疚中走出来了,我在笑。我的情绪好象也感染着同坐的乘客们。他们笑容满面地与我寒暄,让我有了一种回家般地温暖。
我的对面坐着一个纯纯的女孩,她大约是个女学生,也许要到外地去上学。由于她长得很漂亮,我不由得多看了两眼。
发现我在看她,她就起头冲我笑了笑。这时我才注意到她的手中拿着一本《牛虻》。
她抚摩着《牛虻》的书皮,很认真地告诉我:“这本书描写的是灵魂的坚强和不屈的理想。”
一听这话,我哭了。我长这大就从没有像今天一样伤心过。我的眼泪像潮水一样喷涌而出,我的身体不停地颤抖,嘴里却发不出一点声音。
在座的每个乘客,包括那个女孩,都惊奇的看着我。
可是我不在乎,我要哭个痛快,我要让眼泪尽情地流淌,希望可以用泪水洗刷我罪恶的魂